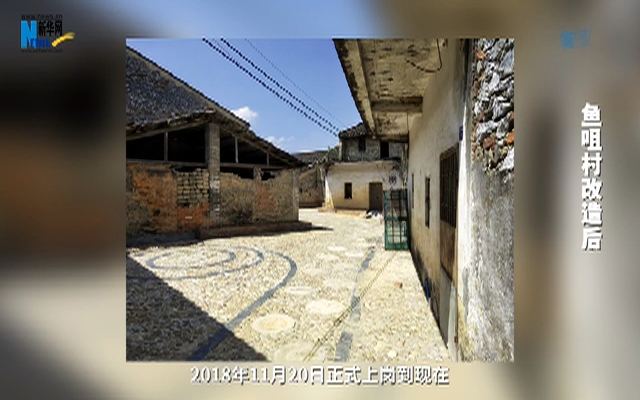夜读 _ 比太阳更温暖的,是爱与希望
书名:《灿烂千阳》
作者:[美]卡勒德·胡赛尼
译者:李继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私生女玛丽雅姆在父亲的宅院门口苦苦守候,回到家却看到因绝望而上吊自杀的母亲。那天是她十五岁的生日,而童年嘎然而止。玛丽雅姆随后由父亲安排远嫁喀布尔四十多岁的鞋匠拉希德,几经流产,终因无法生子而长期生活在家暴阴影之下。
十八年后,少女莱拉的父母死于战火,青梅竹马的恋人也在战乱中失踪,举目无亲的莱拉别无选择,被迫嫁给拉希德。两名阿富汗女性各自带着属于不同时代的悲惨回忆,共同经受着战乱、贫困与家庭暴力的重压,心底潜藏着的悲苦与忍耐相互交织,让她们曾经水火不容,又让她们缔结情谊,如母女般相濡以沫。然而,多年的骗局终有被揭穿的一天……

她们将做出如何的选择?她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关于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灿烂千阳》再次以阿富汗战乱为背景,时空跨越三十年,用细腻感人的笔触描绘了阿富汗旧家族制度下苦苦挣扎的妇女,她们所怀抱的希望、爱情、梦想与所有的失落。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贯穿全书的题眼,这句话出自诗人赛依伯名为《喀布尔》的一首诗,一部描写阿富汗女性的小说为何要围绕喀布尔这一城市,或许是因为,在作者看来,饱受苦难和不公的女性,就是阿富汗这座文明古城的徽标。

在《灿烂千阳》里,两位女主人公玛丽雅姆和莱拉,在强大的父权制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的渗透下一步步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人格的主体性。
通观玛丽雅姆和莱拉的悲惨人生,不难发现,她们的痛苦和灾难都根源于父权制通过社会和家庭给她们施加的压迫。

“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法律是男人的法律,政府是男人的政府,国家是男人的国家”,女性的地位被父权制度所歪曲,处于远离父权文化和话语中心的边缘地位。她们生活在男性的阴影和淫威之下,成为男性的附属物和私有财产,从而使她们的存在仅仅只是一种“作为符号的妇女”,而不是真正意义的自我存在。她们试图反抗,可是“在父权制下,孩子和母亲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依附于男人的地位。并且,由于男人的这一重要性不仅仅是社会性的,还涉及她的依附者赖以生存的经济权力,男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无论在物质或意识形态上,都是十分稳固的”。
强大而稳固的父权制让作为个体的妇女无法也无力抵抗,最终陷于女性自我和本性迷失的泥淖之中。玛丽雅姆和莱拉的遭遇折射出阿富汗千千万万蒙着面纱的妇女的悲惨命运,也是阿富汗所有苦难和灾难的缩影。
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新作《灿烂千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延续了胡赛尼以情动人的细腻写作手法,以温婉平和的方式描述了两个女人之间感人至深的故事。胡赛尼在回复京华时报采访邮件中称,在完成《追风筝的人》之后,他对于创作有关阿富汗女性故事的想法相当着迷,于是就写出了《灿烂千阳》,他希望这本小说能为阿富汗传统妇女增添更多深度、细致与情感的内涵。与前一本小说《追风筝的人》一样,《灿烂千阳》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对于新书取名《灿烂千阳》,胡赛尼解释说,该书的书名源自一首有关喀布尔的诗,“这首诗是17世纪阿富汗诗人Saib-e-Tabrizi在参观喀布尔之后创作的,其末尾词语'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正适合这本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与此同时,这首诗还很适合书中人物即将离开深爱城市时的悲伤气氛。”
胡赛尼坦言创作《灿烂千阳》时困难也更多:“开始创作时,我对是否有能力再创作出一本成功的小说有些疑虑,缺乏自信,尤其是知道有众多读者正迫不及待地想看我的新作品后,我就更加恐慌,我的妻子可以为我作证。但当我提起笔创作,故事情节开始进行时,我就很快融入了主角玛丽雅姆与莱拉的世界,忧虑逐渐消失了。”
胡赛尼说,当他开始写时,他不断想起那些充满韧性的阿富汗妇女。“虽然她们不见得是引发我描写莱拉或者玛丽雅姆的灵感来源,但她们的声音、面容与坚毅的生存故事却一直影响着我,可以说,来自阿富汗女性的集体精神力量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大启发。”
与《追风筝的人》一样,《灿烂千阳》的主角同样面临困境,同样被外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残酷的外在事件所影响,例如革命、战争、极端主义与压迫等。“《追风筝的人》中的阿米尔后来移居美国,逃过了那些令人恐惧的事件与艰难困苦的生活,《灿烂千阳》中的玛丽雅姆与莱拉却亲身经历了苦难。就此而言,玛丽雅姆与莱拉的人生更为困窘。”胡赛尼说,他希望这本小说能为那些世人所熟悉的、穿着蒙面服饰、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的阿富汗传统妇女,增添更多的深度、细致与情感的内涵。

来源:云浮日报微信公众号
图源网络
责任编辑:植发炜 陈小敏
值班主编:区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