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在心底的“年画”
陈碧云
今年春节前,兴之所至,与几位中老年闺蜜在家中包起了角仔,场面温馨热闹。在经历和面、揉包、造型、油炸等一系列的工序后,一筐金黄油亮的油角仔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尝一个,嘎嘎作响、甘香爽脆,满嘴的甜香。甜甜的、香香的,多么熟悉的味道啊!享受着这味道,我们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些过年的画面,就好像播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眼前……
年夜饭,现在被很多人重视,一桌花样百出、美味丰盛的佳肴是大年三十的“标配”。对于少时年夜饭吃什么,我倒是记得不太清楚,但肯定是跟丰盛沾不上边的了。最记得的是老妈的一个菜:包生菜,就是用生菜把自己喜欢的菜包在一起吃。这个菜有着美好的寓意:生生猛猛,生财有道。这道菜年年必有,人人必吃,菜虽简单,却寄寓了对来年的幸福期盼,谁不想那样呢?
过去的年代,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唯一的娱乐,就是年夜饭后,妈妈带我(我是家中最小的小孩)到街上看看属于那个年代的璀璨的灯饰:就是一串串的彩色小灯泡,挂在一些重要的建筑上,例如当时的云浮县委(现云城区委所在地)、县委大院对面的新华书店、银行等。那些小灯泡,一闪一闪的,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在童年的我眼中,是神秘而又美丽的。这样的灯饰,也不多,我有幸住在县城,有机会观赏,也是蛮幸福的了。可能现在好多人不能理解,看几串小灯泡而已,那也算幸福?是的,在那个年代,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对于过年,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除夕晚上和家人一起包角仔迎新年的场景了。没有热闹的春晚,但有零星的鞭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新年正在向我们姗姗而来,那也是一种另类的新年倒计时吧。不会干坐着等待新年的来临,妈妈就带着我们包角仔,这是迎接新年的最后一个工作了。
妈妈会先和好面,然后我们把那面揪出一小坨,放在桌面上,用玻璃瓶把它擀开,擀薄成一大块面片,再用一个小圆口的器物,把面片印出一个个的小圆形,供大家包角仔。妈妈会把一小撮的馅料放在圆圆的面片上,跟着把面片对折,再顺着那半圆的边扭出花边,一会儿,一只胀鼓鼓、两角翘翘的、小巧漂亮的角仔就出来了。包出的角仔,一个一个地放在竹筛上,一圈一圈的围起来,越放越多……这一场景,宁静、温馨,以至于在以后岁月里,一看到那些两角翘翘的小油角,脑海中便会浮现出那一画面,便会想起我那心灵手巧的妈妈。
边包角仔边守岁,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我童年时最难忘的一幅“年画”。但难忘的“年画”何止这一幅呢?
其实为了迎接年的到来,人们在除夕之前的半个多月,便做了许多工作了。印炒米饼,是我们云浮地区流传已久的一个过年习俗,简称印饼、打饼。即使它的准备过程复杂繁琐,但家庭主妇们还是年复一年地去做,在那个年代,不做炒米饼,就没有了过年的气氛。
所以早早地,主妇们便会做好印饼的前期工作。先炒米,炒米的第一步是把米泡一个晚上,然后捞起来,晾干水分,才能放到大铁锅里去炒,这样炒出来的米才会松脆。炒米时,一人烧火,一人炒米。把米炒好,接着要把它磨成粉,磨好的粉,往里面放入一截甘蔗,大概是要让米粉得到滋润吧。磨好的炒米粉要放五七天才打饼。打饼是一个团体作战的项目,一二人不能完成。所以邻里亲戚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了,往往是今天我家打,明天你家打,你帮我、我帮你,你吵我嚷,团结协作,热闹的场面中充满了温情,这是过年期间我们这地方特有的一幅场景。
重头戏是打饼。打饼的过程,是一定不能焦急的。先要把磨好的炒米粉用糖水和好,然后把那些粉装进饼印模里,平整表面、压实,最后把饼从模子里敲打出来。装粉之前,有一个步骤必须要做,就是把花生油涂抹在饼印上,并且要均匀不留死角,这样打印出来的米饼印花才能清晰漂亮,拿来走亲戚才不会失礼。有时候,时间久了,那饼印上的花模会被粉粘住,花纹印不出来,这时候就要用牙签之类的尖锐物把那些粉挑出,让花样重新清晰。印出来的那些饼,此时还不能拿出来见人,还要经历最后的一道工序:接受火的烘烤,成就它的坚硬的身躯。烘烤米饼是一个技术活,要恰到好处的掌握好火候:火过猛会烤焦,过小的火烤出来的饼不香脆。可能是自己一手印出来的饼吧,那时候吃的饼,那是一个齿颊留香,越嚼越有味,令人难以忘怀的。现在社会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过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有炒米饼卖,但在我看来,都比不上小时候自己亲手一块一块印出来、烘出来的饼那样脆,那样香。因为在那米饼里,是自己满满的对少年时过年的亲切回忆。
年末包角仔,炸油角,炒米饼,洗棕叶,包粽子,还有在南山河畔清洗晾晒被子……那一幅幅有关过年的画面,对于像我们这样年龄段的人来说,是共同的集体记忆。她宛如一幅幅年画,已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心田中,永远也抹不掉,随着岁月的流逝,只会越来越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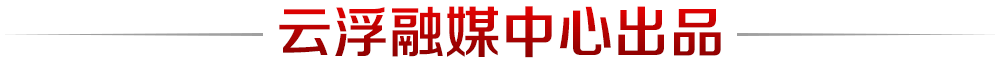
来源:云浮日报
责编:严靖
值班主编:区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