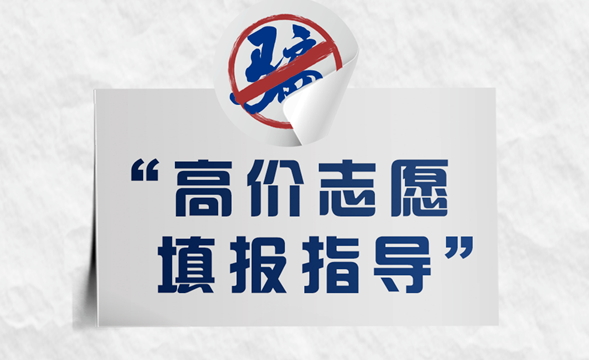百年老街守护人

李晓

 夏日清晨的老街,日出东山,霞光穿过彩云,披在临河老街的吊角楼,披在百年石拱桥上。桥上,一个微微佝偻的身影在挥动扫帚,清扫着桥上轻尘。
夏日清晨的老街,日出东山,霞光穿过彩云,披在临河老街的吊角楼,披在百年石拱桥上。桥上,一个微微佝偻的身影在挥动扫帚,清扫着桥上轻尘。
横跨河两岸的石拱桥,是老街人心里的老祖宗。前年夏天的那场特大洪水,漫过了临河老街的屋顶、树冠,漫过了老桥桥顶,也漫过了老街人狂跳的胸口。
洪水缓缓退去后,老桥露出了稳稳的身子,好多老街人朝老桥深深鞠了三个躬:桥啊桥,您又挺过了这场劫难!但桥墩上的老青石,被咆哮洪水冲到了河的下游。后来修复老桥,这位古稀之年的扫桥人,和居民们沿着河岸一直找啊找,把那些冲到了河滩里的石头一块块都找了回来,修复时重新安放在了老桥身子上。
老桥的扫桥人,一个老街的老居民,一个52年党龄的老党员,和我的年龄同龄,我亲热地叫他“王叔”。王叔扫桥近20年,每当老桥上、老街上传来“沙、沙、沙”如蚕吃桑叶的轻快声,那是漫过老街人心房的宁静乐曲。要是哪天看不见老人扫桥的身影,老街人心里就觉得不踏实,他们纷纷打听,王叔去哪儿呢?
清扫老桥老街,王叔清瘦的身影在老街穿梭,有人问他:“你这样不计报酬地扫街扫桥,到底想图个啥哟?”王叔呵呵一笑说,“老街人都是一家人,大家住在一起,家里干净了心里舒服,我也高兴。”
老街路面上的青石,经人来人往,磨出了石窝窝,那里面也沉积着王叔一年一年走过的脚印。
在老街的四季里,王叔义务清扫街巷老桥的身影,成为老街封面中的剪影。春天,老街春雨细如蚕丝,王叔头戴草帽清扫;夏天,老街河风清凉,王叔带着小铲刀清理牛皮癣;秋天,老街树叶簌簌而落,王叔挥动扫帚打扫落叶;冬天,老街人还在沿用的蜂窝煤炉子里咕嘟咕嘟响,那是老街人在炖肉,街坊们纷纷招呼着扫街的王叔:“来家里吃了走吧”“喝口汤了再走吧”,王叔放下扫帚,摆摆手说:“不用,不用,家里等我回去吃呐。”有时遇到一些街坊里的老伙计,王叔也会进屋子里去坐一坐,同他们聊聊天,聊的大多是老街上的民生事儿。比如说老街路边的哪个井盖有危险得做上一个防护标记,夏天淘气的小孩子们偷偷去河里游泳得去劝阻一下,哪家居民楼院里缺健身器材得帮忙给上面递交一个申请。
这些年,在老街身旁,一座新城拔节生长,老街人抬头上望的天际线,被新城刷刷刷生长的幢幢高楼抬高了。一边是愈发清寂的老街,一旁是日新月异车水马龙的繁华新城。沿着如长蛇状蜿蜒的老街两旁,那些简易店铺里的画匠、篾匠、弹匠、铁匠、锁匠、理发匠,他们用古老的手艺诚恳的劳动谋生,但老街人烟的稀落,让这些谋生的职业也遇到了困境,有的关门停业,有的搬到了新城。在老巷子黄葛树下店铺里画人像的黄师傅,今年夏天准备搬到新城去开店,王叔知道后特地去了黄师傅店里,他轻言细语说道:“黄师傅啊,你走了,我还是来帮你店门前打扫卫生。”一句话说得在老街画像30多年的黄师傅差点落泪。前不久我去老街,遇到了埋头给一个老街大爷画像的黄师傅,他对我说,王大哥那句话啊,把我的心都说疼了,我其实也舍不得老街,就留下来和他一起陪陪老街吧。还有在老街开了40多年理发铺子的陈师傅,店里理发而今实行的还是盐巴一样多年不变的5元一次的良心价,凡是老街出生的婴儿满月后去理胎发,陈师傅一律免费。陈师傅有天告诉我,这事儿是他和扫街的王大哥商量后定下来的。王大哥对陈师傅说,还有啥事儿,比老街添人进口更高兴的事哟。陈师傅一拍大腿说,我这个理发匠,也来帮老街人做点事。
在王叔做楼栋长那几年,老旧小区没电梯,王叔就时常拿着小本子上上下下挨家挨户问柴米油盐的冷暖桑麻事,一些急难愁盼的事情认认真真记在小本子上,再去社区居委会一同商量解决。那几年做楼栋长都是义务,有人问他,何必去做这些费心事呢?王叔依然是那句话:“谁叫我是党的人啊,大事我做不来,我就帮街坊们做点小事情!”
7年前,王叔就和社区的人一起,做起了老街那条河的巡河员。差不多每天,王叔都要去河边巡河,他随身带一个小竹兜,用小铲子铲除杂草,清理河岸垃圾。清澈河水中,摇曳着这个古道热肠老人的忙碌身影。
沧桑老街,在老街人眼里,王叔就是那盏老路灯,闪烁出温暖的光芒,也慰藉着老街人的心灵。


来源:云浮日报
责编:黄韦斐然
编审:黄泳文
值班主编:区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