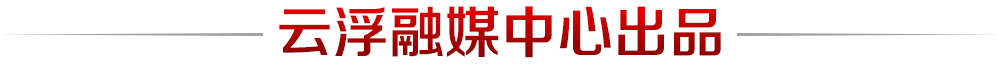酥角情思
苏彩宁
临近过年,超市里的年货让人目不暇接,每当看到包装美轮美奂的酥角,我总有那么几分感慨。
80后的我们,童年时不愁吃喝,但也仅止于饭饱,逢年过节那额外增加的吃食,带来的快乐绝比现在网购一大箱零食要深厚。那时的年货,大多是家里做,粽子、炒米饼、蛋散、蝉虫……我最钟情的还是酥角。
在我记事起,我家每年都会做酥角,这是迎接春节最有象征性的仪式。年底老妈总是很忙,等她忙得差不多,准备好做酥角的材料和工具,在某个最合适不过的日子里,一家人就围在餐桌边,开始热火朝天的包酥角活动。
每次做酥角,老妈总提起她的当年:其实以前的以前过年是不吃酥角的,直到知青上山下乡,到村里插队的广州知青,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教当地人做酥角。当地人学会了,就成了一个习惯,过年都觉有酥角才有年味。那时我总在心里默默感谢那些知青,不仅给我老妈带来美好的往昔,也给我们带来好吃的酥角制作方法,把美好延续了一代又一代。
做酥角是个技术活儿,最难的是和面。高难度的当然老妈亲自上阵,她总是一边和面一边说:放水要慢慢放,一急就稀了不成了。可是她也有失手的时候,她就自我安慰地说:大吃姑娘和稀粉咯!意思是贪吃的姑娘,为了可以吃更多,就多给水,面稀了,就得加粉继续和,面团就越来越大了。我们姐妹几个,会意地一笑,心里应该都有同一句话:做得不好还多理由哦!
等老妈完成和面工程,我们姐弟几个撩起衣袖开始大干一场。洒一层薄粉在饭桌上防粘,掰一团不大不小的面,扯开一些,平铺下来,用一个瘦长的玻璃瓶子,在上面压呀压呀,力度要均匀使往四周,集中在一处就此薄彼厚,当压得四周差不多匀称时,把面块反过来,再压。这是最费力气的活儿,技术要求不算高,一般老二老三来负责,一个累了另一个接力,谁叫她们总嫌我没力气压得久又不薄呢?我就负责用拧下来的电筒头盖,一个个地印出模块来。
我最拿手的是捻花,这还是老妈评出来的,她说我速度快,棱角分明,立体感哪怕是在油炸后仍然保持几分。老二对这只能望洋兴叹,尝试几年后放弃捻花,专心压面了。老三不服气,坚持每年都练习,进步确实有,超越谈不上。老弟呢,刚开始那几年还小,只负责吃,等到大一点,也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只会压皮。所以我是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捻花的重任,轻巧但得技术好呀!
最令人期待的就是最后一个环节了,酥角下油锅。这时,我们都很愿意负责烧火,但要学会控制火候,烧的只能是禾秆,因为火平顺,又容易控制,可不敢烧山草,火猛又一瞬间灭了,这种火不适合炸酥角。不过烧火只需一个人罢了,其他人就一人搬张小凳子,坐在灶前等着,眼巴巴地盯着。灶里火不断,厨房里火烟、热气、香气弥漫,又暖又香。这时不管屋外有没有下冷雨,有没有刮寒风,我们的厨房一定是暖烘烘的,我们的心都是甜丝丝的。这时老妈又哼唱了:灶头有个“霖紧叔”,番薯芋仔快快熟……这在当时我是听不懂的,过了好多年才明白,所谓的“霖紧叔”,是指心急、很想快点有得吃的人。
不一会儿,酥角就出锅了,那个香啊,有种说法是刚出锅的酥角是不上火的,多吃也不热气,真感激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啊。好让我们顺理成章地放开肚皮,吃了一个又一个,老妈这时只是微笑,看着她一年都没吃饱似的几个孩子,不劝阻、不责怪。这时老爸非常恰巧地回家了,“老爸好有食神哦!”我们都嚷嚷,其实我们都知道,老爸是掐好了时间回家的。
过年了,除了摆一碟在神台上,其它的酥角都被老妈藏在一个糖果罐里,然后放到高高的大柜顶上,谁也够不着,好留着慢慢吃。老妈不知道的是,我们几姐弟想吃了,会合伙起来,拿张大凳子,上面放张中凳子,再加张小凳子,两个人扶着,一个人站上去,小心翼翼地,取下那个罐子,每个人抓几个放到裤袋里,偷吃的兴奋和乐趣,至今还能感受得到。
不知不觉间,我们都长大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再也没有自己做酥角了。我是不愿意买超市里的酥角的,哪怕别人做的,棱角那么分明,比我做的要好,但是我不想吃,也许是在避免破坏我记忆里有关酥角的美好。
“当时只道是寻常”,何时再重温美好的寻常?时光再慢一些就好了……
来源:云浮日报
责任编辑:冯浩森
值班主编:区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