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村庄未搬迁,父母乡亲仍生活在那里,守着祖辈留下的山水林田,守着数代人最后的农耕记忆、烟火岁月。父亲常坐在闲弃的石碾旁,抚摸着光滑漂亮的石刻花纹,感叹:“等我们全没了,这村子也就没了。”

诚然,我父母这辈已然成了村里最年长的一代,年轻人已接续不上。这村庄,只是无数离乡人及其后代难再提及的祖籍罢了。故而,我视这些仍在村里生活劳作的人为“守村人”。
土地是根,养活了整个村庄,甚至我竟幼稚地认为,我们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和一季庄稼一样。我虽不再亲近土地,但见到土地依然格外亲近。即便有些已被撂荒,归还给了野草,可那些仍在耕种、繁荣着的,总让我欢喜万分。我也明白了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父亲,为何年逾七旬仍放不下锄头的缘由,用他的话说:“荒了,可惜;种着,就有的吃。”
但凡人能动弹就不闲着,土地也就不闲着,整个村庄也就不闲着,依旧欣欣向荣,生气满满。如此,像我这样客居他乡的游子就觉得“根”还很有劲儿,还扎在故乡沃土里,心有皈依。
俗话说:“舌品天下,胃知乡愁。”无论走多远,儿时家乡的味道永远也下不了舌尖。这不,定居北京的小杜回村看望二老,临走时行囊里塞满了母亲做的缸炉烧饼、腌腊肉、卤水豆腐、辣椒酱,以及村里才有的地道的柴鸡、笨鸡蛋、红薯、土豆。小杜说起来眼泪汪汪:“等父母不在了,我去哪儿吃这好东西。”我深以为然:“那就常回来。”
许是人到中年,越来越想回村转转,穿行于鸡鸣犬吠、林荫清风、新老民居之间,寻找新时光里的老手艺、老物件,那种年代感、穿越感,我很享受。
那日,不经意走进一所老宅院,主家是称作二爷爷二奶奶的。推开斑驳的贴了门神的老木门,见一株梨树、一株李子树繁花盛开,满院飘香;扎了荆条篱笆的小菜园已锄过,像是种了什么,过冬的春韭、羊角葱已近两拃高,能想象得到那浓郁的鲜香。二爷爷操着很难见到的墨斗、刨子、凿子等工具,专注地做着木工;二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做着布艺坐垫。一只黄猫、一只黑猫躺在花窗下的蒲团上,慵懒地晒太阳,抬眼又闭上,算是打过招呼。
我高声喊:“在家呢?”二爷爷转过身说:“回来了?不用太大声,我听得见。闲着没事儿,打几个板凳。”二奶奶搭话:“要搬到危房改造的新家去,他打板凳,我做坐垫。”他俩一个木工好,一个针线好,近七十岁了还没撂下。进屋参观,还是儿时我来串门儿时的陈设。依稀记得曾登着圈椅读年画,站在挂镜前做鬼脸,提起茶壶倒水喝,瞅着收音机听评书;老花瓶插着新杏花,老酒壶应该灌了新烧酒……二老边忙活儿边与我聊天,久违的平和、温馨令我彻底放空,捧一只绒绒的鸡雏在手心端详,沉浸在这美好的春日农家小院里。
村里的张大叔还养着蜜蜂,话说有30多年了;万大叔的烧酒坊还开着,经年老酒更加醇香;张大伯经常摆开阵势,编了精致篮筐笸箩自用或送人;杨大娘做虎头鞋、虎头枕、千层底的手艺一点儿没丢;不少妇女常凑在一起研究怎样把花馍蒸得更漂亮……如此这般,我很感动。老手艺在,老物件在,村子的魂就在,不老的乡愁就在,乡村振兴就有根基与希望。
“守村人”是村庄的宝,他们固执地守着传统老宅老院、朴素民风民俗,守着一方水土一方人,守着数代往事数代情。眼见他们日益年迈,慢慢老去,一个个陆续归于故土,在村里出生,又在村里逝去,难免有些伤感。可他们深深的皱纹、浅浅的谈吐中,藏着生活的智慧、人生的豁达,引我常回村与他们坐在台阶上、门槛上、老街口,聊聊过往,守着当下,不去也不敢提未来。
去年,邻村回来个返乡青年小周,说是要在村里搞乡建,把艺术植入故乡。教农民画画,“推销”璀璨星空,吸引文艺青年进驻创作;回收老物件,发展民宿旅游,让将衰的村庄在新时代复活。我清楚,邻村大,有产业,有人气;我村小,注定行将消失。可有年轻人愿意来“守村”,又点燃了我心中的光亮。终有一天,我也会加入小周的团队,住回村里,做个无愧无悔的“守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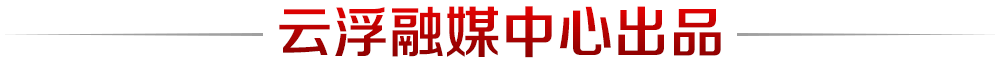
来源:云浮日报
作者:张金刚
责编:胡焕红
值班主编:区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