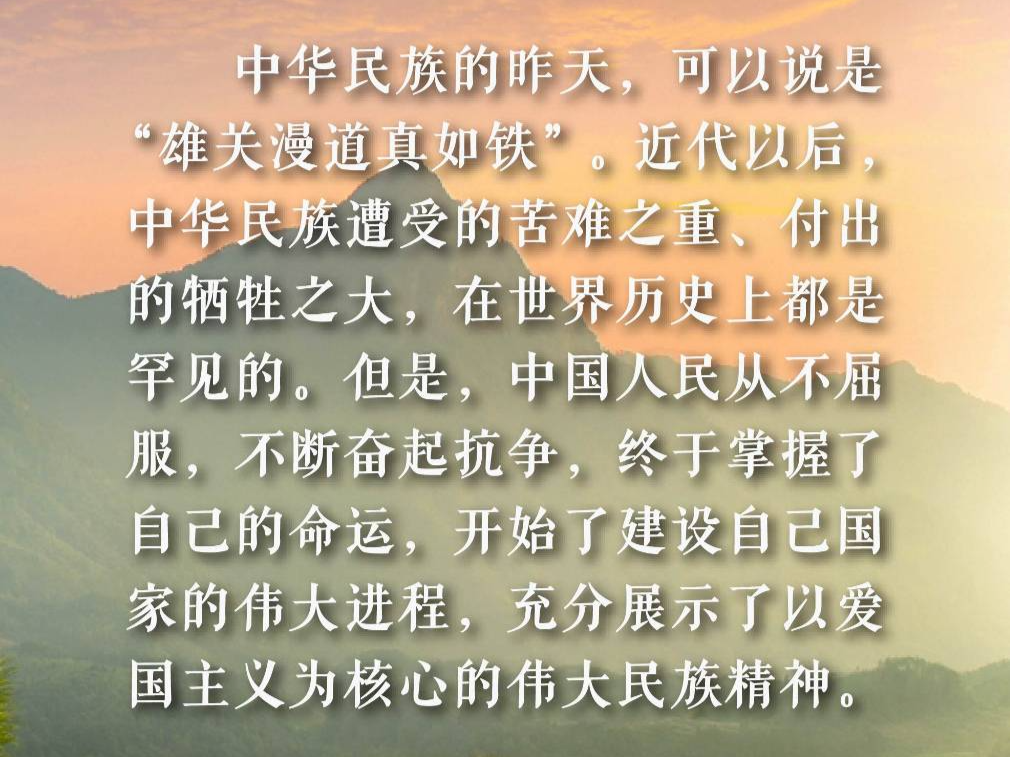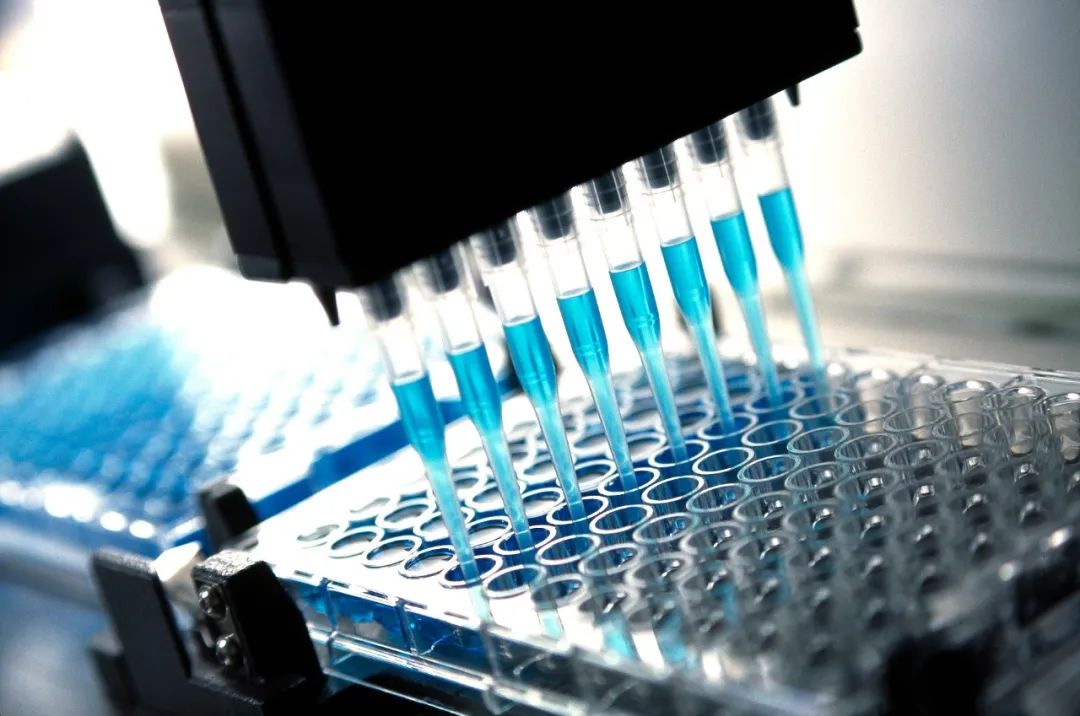夜读 老家啊老家

老家啊老家
▭作者:李晓

老家,在中国人的节气里,故土情结蒸腾扩散,是最容易被追问的一个话题,被引颈眺望的一个地方。
到底哪里是老家?是生命里第一声啼哭传来的地方,或是寄托我们情感归宿的源头。大地之上,曾经拖家带口的祖先,从一个驿站飘摇到另一个驿站,最后把一个家安顿下来,那里便会成为我们的故土老家。
寄予我们思念的地方,是老家。总觉得在城市里出生的人,对老家这个概念模糊而遥远。比如我的儿子,我问他,老家在哪儿?儿子说出一条街巷的名字,那是他生命摇篮的某一栋楼房。儿子的回答让我失落不已。
83岁的老父亲问我,你知道老家在哪儿么?我在阳台上指了指能看见的群山轮廓,它耸立的脊背在天空下呈奔跑的姿势,有着祖祖辈辈生命的绵延。

其实我出生的那一片乡土,就在距离我所住城市的8千米之外,从我而今居家的窗前,如果不是雾天,可以隐约窥见我故土的山梁。故土于我,就是随时贴在窗前的一枚邮票。
我的故土,实在是离我太近了,太近了的东西,实在是缺乏深沉的想念。家住东北辽河边的诗人老柏,离开故乡已经40多年了,这些年腊月里常坐火车回去过年。父母早不在人世了,但故土的山山岭岭还在一声声喊着他的乳名回家,辽河边起伏如浪的芦苇丛中,还有童年的记忆在等他拾起。老柏的诗里有一句,他说在而今距离遥遥故土的城市,深夜里辽河边伸出一个万里之外的鱼钩,他鱼一样咬钩了。我被这种情绪浸染,我对故土的虚构,也建构在一片茫茫黑土之上,旷野蓝天下,是我奔跑的渺渺故乡。
有一年秋天漫游东北大地,肥沃黑土如凝固的油,庄稼如浪。我看到一处竹篱笆四围的土墙小院,我几乎是扑过去,抱住油烟风尘中已是黑黢黢的老墙,一瞬间把它在心里认领成了我的故土老宅。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我气血中的熟悉气味,或许,我的前世就降临在这里。
每次去父亲那里,腿脚不方便行走的他,心心念念的一句话就是,啥时候陪他回老家看看。老家在父亲心里,是一棵不断生长的老树。

6年前的春天,父亲病后出院,我带着他回老家去看一看。那次父亲站在山梁望着老家土地上郁郁葱葱的植物,微微张口,感觉是在把故土山地里的气息一口一口认认真真地吸入。
父亲22岁那年离开故土,成为村子里第一名专科生到县城工作,却一直在故土老家里来来回回。我母亲还是一个地道农民,父亲四个兜的中山装里插着写文件的笔,老家的责任田地里也有锄头镰刀在那里等着他。父亲退休后,母亲进城,故土老家成为父亲紧紧攥在手里的一张情感老“存折”,他一次一次地在心里攒着对老家乡土上的沉沉感情。比如念叨着乡土人事,某老汉生日了不忘随一份礼,某大爷亡故了送上一个花圈,某大娘家孙子娶亲,还要亲自去吃上一顿喜酒。和老家乡亲们握手感叹“见一面少一面了”。某年老家干旱了,还慌慌张张联系一个在气象局工作的后辈,让他们通过人工降雨方法把雨打下来,甚是傻气天真。最深刻的记忆是机场建设那年,老家的土地被征,父亲望着那棵皂荚树被连根拔起,巨大根须如牙齿的呼喊,我看见父亲的双腿直颤,他用力扶在一棵树上,身子已经站不稳了。
这些年,我怀着小悲悯与渐大的包容之心,对故土老家的记忆与保藏,让那一片弹丸之地持久地发酵,酒一样醇香。我的朋友郑哥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怎么能够没有故土老家储藏呢,老家是心上的一口井,源源不断地赐予我们的心田,长出一片小小的绿洲,托起了一生的命运。
这么说,我是一个有老家的人了,我身体里的信号,能够感受到老家对我源源不断的情感发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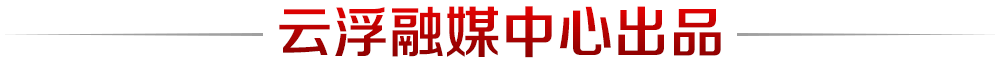
来源:云浮日报
音频:莫颖琳 | 剪辑:潘伟
责编:黄泳文
值班主编:区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