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清明的深处
李晓
凝望故国诗词里的清明,雨水似乎一直没有停歇。清明时节为什么雨纷纷,那从天而降的银亮丝线,是不是连接两个时空中奔跑的灵魂,穿过迢迢山河,在密集的雨水里再次相拥。
清明前后的夜里,梦亦如这个季节里的雨水一样频繁。绵绵雨水披挂在山野林木,我凌乱的梦又栖息何处。
在这些梦里,我那些逝去的先人们,从云深不知处里踏云而归,与我亲近,恍然感觉他们还一直住在我的血液里,一同奔腾。先人们在梦里如最早的黑白电影,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梦,还没有梦到过彩色的画面,难道一个人的梦,从大脑的最深峡谷里分泌出来,穿过幽幽暗暗的长长隧道,被一层一层滤尽成了记忆深处的黑白色。
有人说,一个人真正的死亡,是在记忆里被永远地抹去,而清明,是复活集体记忆的盛大日子。在一个国家这样最具古典传统气象的清明节日里,我们追忆遥望祖辈先人,涌动着雨水一样密集的思念,发酵着对先辈先贤们无限的感念感恩,这样一个节日所承载的重量,是与大地山河同在的,它如春山春水一样,万古在,万古流。
一年之中,到了清明,我那迷信的妈,表情就庄重肃穆。有一年清明,一只飞蛾绕着屋里灯管扑闪几圈后,落入客厅地板,飞蛾在地上缓缓蠕动,我妈赶紧双手合十,嘴里嘀嘀咕咕。我妈说,这肯定是哪个去世的老先人回来看一看了,不要惊动它噢。我妈端坐沙发上,陪伴着那只直到半夜才飞走的飞蛾。
清明,在千年时空流转的大地上,是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节日。这种习俗,被我妈这样一个淳朴的农民传承着,于我,又成了一个“火炬”的传递者。无论乡下还是城市,我妈在清明节里,总爱摩挲着找出一些祖辈亲人留下的照片,擦拭着照片上的灰尘也擦拭着浑浊的记忆,我妈一一端详着,在脑子里回放着他们生前的面目姿态。而那些连一张照片也没留存世间的逝去亲人们,我妈就只有反反复复搅动记忆深处里的故人气息了。我外祖父外祖母,在我妈十多岁时就离世了。有一年清明,我妈在城里回忆着他们的往事,泪水扑簌簌地往下落。清明那天中午,我妈做了一大桌菜,在碗上搁上筷子,又倒了酒,在我妈“爸爸妈妈回来吃个清明饭”的呼唤声中,我打开房门,恍然感觉在烟云氤氲的青绿大地上,我从未谋面的外祖父外祖母和逝去的亲人们依次回来,在这清明节的一顿热饭热菜里又神秘地相聚了。我,又踏踏实实地焊接在了世代生命绵延的链条上,我明白,只要这链条上哪怕是掉了一颗螺丝帽,我这个生命或许就不再是我。
清明的雨水,为大地山河梳妆,或许也是清洗擦亮一下我们迷蒙昏沉的心灵,让我们明白生命中那些随风而逝的离别,是分分秒秒在发生的事。
想起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下班后和单位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一位同事说,桂花路边有一家新开张的馆子味道不错,改天一定请你们去尝一尝。这位同事还带着歉意说,来单位这么多年了,还没请你们好好吃一顿饭,请多谅解啊。没想到他的邀请,竟成了留给我们的遗言。当天晚上,他突发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在写给他的悼词里,是我们无尽的追思。朝夕相处的十多年岁月,我们在一幢大楼里工作,每天在同一个单位的食堂里吃着相同的饭菜,喝着相同的汤,看对方喉结滚动……有次一同出差住在小旅馆里,这位同事曾向我谈起过他的家庭,我这才知道平时他为啥显得有些吝啬,一双破了洞的袜子也要缝一缝,一支牙膏也要挤了又挤,是因为他瘫痪在床的母亲需要长期吃药和护理,他的妻子也多病,整个家庭就靠他一个人撑起。在他去世后念叨起这件事,走进了他那简朴的家,我们才发现,他的那些吝啬,他的那些节俭,他的那些舍不得丢掉一张旧报纸的行为,其实是一个男人默默无言的美德,是对一个家庭的责任和担当。想起曾经私下给他起绰号“铁公鸡”,同事们在他的遗像前鞠躬,表达着内心的愧疚。
在清明的深处,让我们对美好人间的所有生命,都心怀关切地道上一声祝福,道上一声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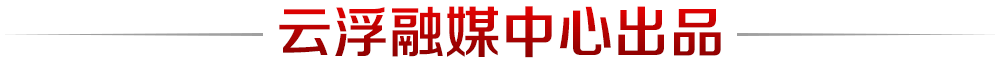
来源:云浮日报
责编:严靖
值班主编:区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