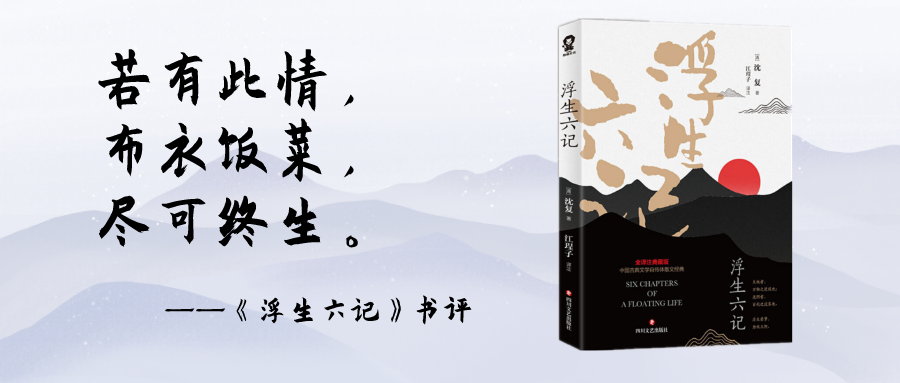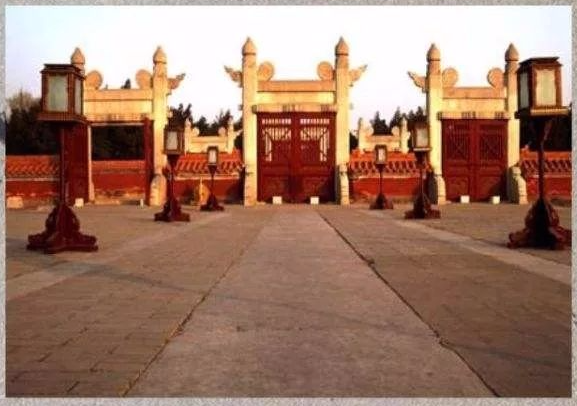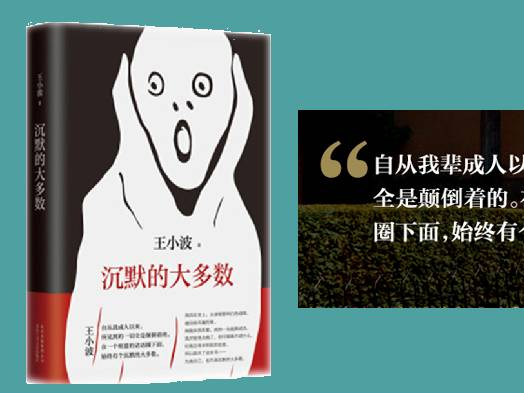双城记

书名:《双城记》
作者:〔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宋兆霖 译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月,那是愚蠢的年月;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都直奔天堂,我们都直下地狱——总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时代如此相似,以至当年有些显赫一时的权威人士坚持认为,无论对它说好说坏,一概只能使用最高级的比较词语。——《双城记》

双城记的“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正直善良的马奈特医生由于告发贵族的恶行被投入巴士底狱,他的孤女露西被接到伦敦抚养长大。贵族青年达内憎恨自己家族的罪恶,放弃家族财产到伦敦当了一名法语教师,与露西产生了真诚的感情。马奈特获释后以宽厚的胸怀原谅了达内家族的所作所为,同意了他们的婚事,然而达内却遭到来自底层、对贵族怀有极大仇恨的德发日夫人的不断陷害……

故事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连结起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围绕着马内特医生一家、德发日夫妇为首的圣安东尼区展开叙述。通过双线并行的叙述手法,呈现出了一个善恶交织、爱恨兼有,智慧和愚蠢共存,光明和黑暗搏斗的世界。
我看到从这个深渊里升起一座美丽的城市,一个卓越的民族。经过未来的悠悠岁月,在他们争取真正自由的斗争中,在他们的胜利和失败里,我看到前一个时代的罪恶以及由它产生的这一个时代的罪恶都逐渐受到惩罚,消亡殆尽。——《双城记》

攻占巴士底狱
中国学者、作家梁实秋曾对《双城记》如此评价:仇恨是痛苦的,而痛苦的仇恨应该用仁爱及人道去化解,作品没有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却因此而造就了大革命的气氛,化解了暴力行为,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浪漫色彩。

《双城记》中的社会充斥着流血,杀戮和报复。革命人民丧失了理智和人性,他们杀人并以此为乐事常事,并为之冠以正当的理由:为这个“自由、博爱、平等,要不毋宁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除掉任何一个不利于它的人。失控的革命演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革命人民在疯狂报复,盲目屠杀他们所憎恨的压迫群众的贵族的同时,也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阶级,成为自己所憎恨的暴虐残酷的代表。而唯有博爱与仁爱,才能救赎这个畸形的社会。
自由涉及个人的独立选择,平等涉及资源的分配,博爱则是个人修养,大革命的雷霆之力打破了之前的阶级,使得一切有了重新洗牌的可能。但动荡不安的时局让嗜权的政客有了可乘之机,被激情操控下的群众则只剩下疯狂和盲目。唯有好的制度来保障自由、实现平等。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一直都是人类孜孜不倦予以探索的。
狄更斯无法找到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答案,却能让我们通过阅读《双城记》来厌恶贵族的趾高气扬、害怕群众的粗鄙狂乱,进而让我们对于苦难之下的人产生同情。一个人的同情固然微弱,但若人人都持有同情之心,人人都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一个人的爱就汇成了博爱。
查尔斯·狄更斯,英国小说家,出生于海军小职员家庭,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曾在皮鞋作坊当学徒,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后担任报社采访记者。他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不同年龄段的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
他生活在英国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这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但同时他也宣扬以“仁爱”为中心的忍让宽恕和阶级调和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抱行动上支持而道德上否定的矛盾态度,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和软弱空想。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和描写1789年法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前者展示了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并批判了为资本家剥削辩护的自由竞争原则和功利主义学说。后者以法国贵族的荒淫残暴、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威力,来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预示这场“可怕的大火”也将在英国重演。其他作品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来源:云浮日报微信公众号
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植发炜 李艳
值班主编:区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