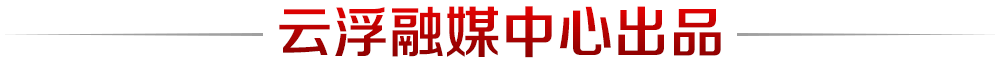春天的夜里,老家的树常把我摇醒。在迷迷糊糊的睡梦里,我看见树们在故土山坡上整齐列队,伸出的枝丫,似在拍着手,欢迎我回家。
有天一大早,父亲给我来电说,他梦见老家的桃树开花了,红彤彤的让人睁不开眼,让我一定回去看一看。父亲说的那些桃树,当年也有他的培植,有一些桃树的苗子,是他当年在县城工作时托关系从邻县买回来的。
不过最让父亲牵挂的,还是老家那些亲人们栽下的树。比如那棵皂荚树,伫立在我老家村头一个叫做水井湾的地方,是我奶奶1935年出嫁到这里时栽下的。
我奶奶81岁时来到了城里居住,她87岁那年就痴呆了,已经认不得我爸了,偶尔喊我爸叫“叔”。不过她还认得钱,依然眉开眼笑地接过我给她的钱,裹在一张老旧的手绢里,再用麻线一层一层缠上,有一回奶奶把钱塞给我说:“你给我买一套房子,看够了不?”我打开,有700多元。我奶奶是90岁那年春天走的,她留下的遗产,就是那手绢里一直包裹着的1200元钱。我奶奶的坟,就在她当年栽下的那棵皂荚树下,奶奶,愿你在树下安息。
我爷爷也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美德之人,他活了73岁,栽下的树有上千棵,这是大队里的宋会计简单统计的。我奶奶回忆我爷爷说,他在月亮下栽树,饮水,施肥。我们那个荒凉的山坡,就是我爷爷带头栽下的树,有桃树、李树、梨树、柿子树、苹果树、橘子树,还有香椿树、苦楝树、青冈树、槐树……
我爷爷是个高瞻远瞩的农民,他一直认为不能靠种地过日子,还要种树,尤其是多种经济林木。我爷爷做过生产队长,有一年被公社评上劳模受到过县长接见,这成为他一生中的至高荣耀。有一次他患病住在医院,突然挣扎着爬起来对一旁的大队干部说:“我得病住院,县长不会知道吧,千万不要麻烦他来医院看我了。”大队干部严肃地说:“老李,你就别多想了,县长为了全县的工作操心劳累,听说连睡觉的时间也是硬挤出来的,哪来的时间看你啊。”我爷爷突然感到很委屈,又要从铺上爬起来,声称要到公社去打一个电话,给县长汇报一下生产队里植树造林的工作。
我爷爷死的那年,还没实行火葬,他的寿棺,生前就用他栽的林木打制而成。我爷爷是个对生死看得很开的人,记得他夏天常常爬到堂屋中摆放的棺材里去午睡,有一回午睡起来咳嗽了一声,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爷爷的坟,就在他种下一片树木的山坡上。20年前的春天,在我老家山坡不远处,要建一个机场,山坡要爆破碾平,爷爷的坟也要迁移,我和几个堂弟打开土坟,只见里面的棺木已腐烂不堪,爷爷的尸身也成了几块白骨,白色头骨内,还有几颗惨白的牙齿,像是在呼喊。爷爷的坟迁移后,几个孙辈在他坟前栽了松树柏树,每到春节清明这些传统节日,我们都要回到老家去祭奠,在爷爷的坟前树下相聚,也算是一年之中在老家的团聚。在坟前一棵松树上,鱼鳞般的树皮上有透明的汁液溢出,像从树身里缓缓流出的泪。
在我老家,还有许多亲人们种下的树,我每次回去,总奇怪地感到,这些树上,似乎都保存贮藏着亲人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匍匐在大地上的身影,就是树们被大风吹弯了身子的姿势,在这些树的DNA里,流淌延续着当年种树亲人们灌注的血脉。
树有灵犀,这些亲人们种下的树,在树梢上,悬挂着我精神的罗盘,将我眺望老家群山大地的视线,永远地相系相连。